
在高净值群体和家族财富管理圈,往往有人把“信托”神化,似乎只要把资产装进一个离岸信托,就能高枕无忧、彻底隔离债务、逃避追索。
2025年9月,中国香港高等法院对许家印家族信托案所做的一纸判决,令这一幻想崩溃:判令授权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包括其离岸信托持有在内的资产,将“资产隔离”的信托防火墙“一举击穿”。
这一案例不仅震动中国,也在全球财富管理界掀起风暴。它提示我们:信托绝不是天然的“法外岛”,其安全性永远建立在合法架构与诚信原则之上。

一、什么是真正的信托?
在法律上,信托(Trust)是一种财产安排:委托人(Settlor/Founder)将特定资产(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Trustee)管理,目的是为受益人(Beneficiary)或特定目的,以信托契约(Trust Deed 或其他信托文书)明确权利义务。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负有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y),必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为优先,遵守契约条款并合法运作。

图/许家印,来源:网络
1、信托的关键特征包括:
资产所有权分离:法律上,信托财产归受托人名下,但其使用与受益权属于受益人或信托条款所限。
义务约束:受托人不能自由处置信托资产,其行为受契约约束,并需为其行为负责。
不可任意撤销/变更(视信托性质而定):有些信托为可撤销(revocable trust),但在许多高净值家族传承规划中,多为“不可撤销信托”(irrevocable trust),以确保资产与设立人脱钩。
目的或受益人明确:信托设立之时,应满足确定性原则(确定性意图、确定性财产、确定性受益人),即信托的目的、财产和受益人须明确可识别。
2、在理想模式下,真正的信托拥有以下几个基础要素(即信托架构的“底线”):
委托人必须真正放弃控制权:无撤销权、无单方面指令权;
受托人必须具备客观独立性,不受委托人直接操控;
信托财产的来源须合法、清晰,不能是用来隐藏非法所得或规避债务;
设立时间应考虑债务风险:若在已知有债务风险时转移资产,容易被质疑为欺诈转移。
3、信托契约条款应合理、透明、能被法院审查
只有满足这些要素,信托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资产隔离”“债务保护”的功能。若信托只是挂名安排,而实际控制权仍被委托人保留,则信托很可能只是“名义信托”,法院也可“穿透”(pierce)信托形式,回到实质层面进行认定。
值得强调的是,信托并非万能:它在税务、监管、跨境执行、债权追索等方面都有复杂风险,并非“法外保险箱”。许家印案,就是对这种神话的最典型反驳。

图/恒大集团,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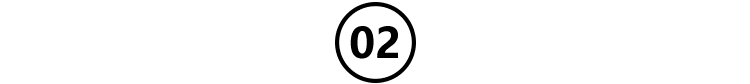
二、许家印信托在香港被击穿的3大法律理由
虽然不少文章称“许家印的信托被香港击穿”,但严格来看,目前香港法院尚未宣布那一层信托在实体上彻底无效。但从判决内容、法律逻辑与媒体公开论述,确可总结出法院“可击穿信托”的三大法律理由。
以下归纳如下:

下面逐一深入分析。
1、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透视“名义”信托背后的控制权
在普通法体系下,信托虽有严密的形式结构,但法院不是只盯着形式,而更看重实质控制。若委托人在形式上把资产给了信托、交给受托人,却在实质层面继续控制、支配,那么法院可能认定这是一个虚假信托(sham trust)或自益信托(self-benefit trust)。
在公开资料中,多家律师和法学评论指出:在许家印案中,信托架构被怀疑存在以下情形:
委托人保留投资决策权、资产替换权、更换受益人权等核心权能;
受托人名义上管理资产,实际上受委托人干预操控;
信托收益分配、资产安排体现高度家族意志控制。
这些都使得信托形式与实质脱节。香港法官在判决中也援引类似普通法原则,强调“透视实质控制”、“不能被法律形式所误导”。据媒体报道,法院以此为依据穿透信托结构,将信托资产纳入可接管与冻结的范围。
在判决书中,法院援引了英国高等法院 Edward Bartley Jones QC 在Dadourian Group & Others v Azuri Ltd的论点,强调即便是 discretionary trust(全权信托),如果实质上为被告控制,也可受到 Chabra 管辖权(即法院对第三方的冻结令管辖)制约。
换句话说,即便信托安排再复杂、层层离岸,如果实质上受委托人控制,法院有可能绕开形式,直击实质。这正是“信托击穿”的第一道门槛。

图/2009年11月5日,在香港恒大上市会议上的许家印,来源:慈善家杂志
2、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非法脱身不可承受
即便信托结构设计得再合理,如果资产注入行为本身具备 欺诈性转移 的特征,也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或被撤销。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在香港破产法框架中,都存在相应法律机制(例如《破产条例》或破产撤销权条款)允许法院对恶意转移资产行为进行追溯和撤销。
在许家印案中,清盘人提交的证据披露:
恒大集团在2017年起就累计埋下巨额财务漏洞;
然而在风险显现之前,许家印将个人资产通过离岸公司层层注入信托;
许在信托设立时,对恒大财务状况、资本链断裂的可能性应有认知;
这种在债务或财务危机前夕突然转移资产的操作,极具欺诈性转移典型特征。
法院在判决中强调:“债务人不能一边拖欠巨债,一边用信托给自己和家人保留巨额财富”。由此认定,若资产转移行为具有规避债务、欺诈骗债的目的,则不应受到信托制度保护。
这就是信托杀手之一:即使信托形式安排得再精巧,只要资金来源与目的具有规避债务嫌疑,那信托本身就可能成为可撤销之安排。
3、信托独立性缺失与债权人保护优先原则:制度逻辑上的破壁
第三个逻辑支撑是:信托的独立性如果缺失,那么其“隔离”功能将丧失;再者,在破产清盘程序中,法院往往依据保护债权人优先的公共政策,愿意向信托进行“接管”“冻结”或穿透秩序。
信托的资产隔离功能建立在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真正“脱钩”的前提之上,即受托人独立管理、不受委托人控制。但在许家印案中,法院认定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高度关联、控制权未真正分割。这使得信托的隔离功能在实质上被否定。
其后,法院进一步认为:在债务危机与破产清盘情形下,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是一项公共政策优先原则,法院可以突破信托结构,在必要情况下对信托进行接管、冻结或返还。
在香港法律中,《信托承认条例》(Recognition of Trusts Ordinance,Cap. 76)是承认信托效力的基础,但该条例也明确规定:受托人无力偿债或破产时,该信托资产不得成为其财产一部分。也就是说,当受托人破产时,其债务人不能主张信托财产。
此外,香港法院依据普通法原则和破产法规定,授予了接管令(receivership / managerial takeover),冻结令(freezing / Mareva injunction),披露令等程序性工具,以保证债权人的合法追索。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接管人为识别、调查、保全资产而被授权的职能,并未立即改变资产所有权,而是程序性手段;但若后续能证明信托安排无效或可撤销,那么信托资产可能被实质性“击穿”。
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书中并未明确断言某一层信托已被实体性“击穿”。媒体关于“击穿信托”的说法多来自于法院授权清盘人接管广泛资产、冻结信托层面的行为,但这在法律上更多属于程序性保全,而非信托契约本身被撤销。然而,这已经是对信托安排的极强冲击。
总而言之,这3大理由:
香港方面指出,许家印虽名义上把资产转入信托,却保留了投资决策、更换受益人等核心控制权,受托人沦为“傀儡”。更关键的是,恒大早在2017年就埋下财务黑洞,许家印明知公司危机四伏,仍在2019年危机爆发前突击转移资产,这明显属于“欺诈性资产转移”。
香港法院“击穿”许家印家族信托所依据的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
首先是“实质重于形式”,不管信托架构多复杂,只要委托人能实际控制资产,就不算真正的独立信托;其次是“反欺诈原则”,债务人不能一边欠着巨额债务,一边用信托为家人保留财富;最后是“债权人保护优先”,在大规模债务危机中,法律更倾向于维护被欠薪、欠房款的普通债权人权益。这三大法理支柱,让许家印的家族信托防线被“击穿”。

图:许家印、丁玉梅 夫妇,来源网络

三、新加坡vs香港:
信托制度的优势对比与家族信托布局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两个主要的财富管理中心,信托制度的对比也备受关注。尤其是在大陆高净值人士眼中,选择香港/新加坡信托往往成为“财富避风港”策略的一部分。
通过对比两地制度与实践,以下几点尤为值得注意。
1、新加坡信托制度的突出优势
以下是新加坡在信托领域常被强调的优势,也是其能成为亚洲信托中心的基础:
优势与具体体现与法律依据分别如下:
①高度保密性:新加坡信托不设公开信托登记,信托契约、受益人信息一般不对外披露。若受托人为持牌信托公司,其有法定义务保密,泄露信息可承担法律责任。
②税务优惠机制:新加坡对非新加坡来源的投资收益通常不征所得税;信托财产交易、分配也可享有资本利得免税、无遗产税、无赠与税等优惠。
③立法与监管框架完善:信托受《受托人法》(Trusts Act)、《信托公司法》(Trust Companies Act)等法律监管,持牌信托公司须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注册并受监管。
④契约灵活性与可定制性:委托人可设定保护人(protector)、分配规则、信托期间、再投资条款等,具较高可塑性。
⑤法律可预测性与稳定性:新加坡法系承袭英国信托法传统,司法体系成熟、案例丰富,法官解释也趋于稳健,可为家族信托安排提供可预期性支持。
⑥继承规则屏障:新加坡信托不受强制继承法(forced heirship)规则干扰。《受托人法》第 90(2) 条明确,若按照适用法律有权设立信托,则其与继承有关的规则不得影响信托的有效性。
在实际运作中,新加坡信托还常被用于资产隔离、财富传承、税务优化、家族治理等目的。其制度设计使得高净值家族在面对跨国资产、多代继承、法规变化时具有更强应对能力。

图/新加坡,来源:网络
2、中国香港信托制度的特点与局限
中国香港虽也有信托制度基础,但相比之下,其优势与局限更为明显:
①特点与优势:
香港承认信托关系,《信托承认条例》(Cap. 76)将海牙信托承认公约纳入香港制度体系。
司法体系成熟、执行力强、与国际接轨,香港法院在跨境资产冻结、清盘接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与权威性。许家印案正体现出香港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对信托关系的审查与执行能力。
接近中国内地,语言、文化与市场接轨优势明显,对于大陆高净值人士设立信托布局更便捷。
②局限与风险:
信托防线被穿透的法理风险较高:
如许家印案显示,当信托安排被怀疑用于避债、控制权实质保留时,香港法院具有较强意愿与能力突破信托结构。
税务制度劣势:
香港信托在税务优惠方面并无重大设计,信托收益、资本利得等部分可能面临税务制约。相比新加坡的免税机制,香港的税务诱因不足。
公共政策倾斜与债权人优先原则:
在破产清盘程序中,法院往往站在保护债权人的立场,对信托进行保全、接管或穿透审查,信托安排容易受到挑战。
信托透明度与披露压力:
在重大诉讼、披露令、冻结令等情况下,法院有权限要求披露信托结构、资产、文件等,信托隐私保护与保密性较难获得彻底保障。
信托法律制度相对薄弱:
虽然香港法律承认信托,但其本身信托法体系并不如新加坡稳固;在信托法制度创新、信托监管、受托人监管方面欠缺完善立法。
因此,对于将信托作为财富隔离和债务防护工具的高净值人士而言,香港信托在面对极端风险事件时,可能并非最安全选项。

图/中国香港,来源:网络
3、对比总结:新加坡胜ْ香港的几个关键点:
从上述优劣对比来看,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关键判断:
①保密性与隐私保护:新加坡更具优势,信托安排更难被轻易窥探
②税务效率:新加坡在非本地收入、资本增值、遗产税、赠予税等方面更优惠
③制度可预期性与法律支持:新加坡在信托法制度完善度、司法判例累积方面更稳定
④破产追索抗风险能力:虽然无制度完全保险,但新加坡信托在资产转移、设立时间、控制权分割等处设计得当,可降低被穿透的风险
⑤地域与市场接轨:香港在接近中国市场、便利性、语言文化接近性方面占优
因此,在家族信托布局时,许多专业律所与财富管理机构更倾向于推荐以新加坡为信托架构核心,再结合其他离岸司法区做补充(如开曼、BVI、英国等)。
但必须强调:即使在新加坡,信托也并非不可触碰,若信托安排设计不当、控制权保留过多、设立时间不合规、资产来源存在疑点,也可能遭受法院或跨境追索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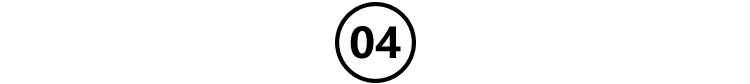
四、对高净值人士与家族信托布局的策略建议
以许家印案为镜鉴,对于真正希望通过信托进行资产保护、财富传承的家族与个人,以下策略与原则值得重视:
1、合法与合规始终是底线
合法资产来源:信托注入的资产必须合法、清晰,避免涉嫌非法所得、逃税、洗钱等风险;
避免明确存在债务危机时转移:若在已知或可预见的债务风险之际设立信托,极易被法院认定为欺诈性转移;
避免过度保留控制权:委托人应尽可能放弃核心控制权(撤销权、投资指令权、资产替换权等);
合规披露与配合司法:面对法院披露令、冻结令等,积极配合法院调查、披露信托文件,有利于争取信托保护。

图/2017年3月28日,香港,许家印参加中国恒大2016年业绩说明会。来源:慈善家杂志
2、结构设计务求“可穿不破”而非“不可攻破”
把信托设计成不能被法院“击穿”的思路恐怕不现实,关键在于使其穿透成本极高、难度极大。具体可考虑:
多层信托结构设计(如母信托+子信托);
受托人与投资管理分离、独立专业受托人;
保护人机制(Protector)控制变更受益人、受托人更替权,以制衡;
设定“备用信托”(Contingent Trust)安排,以应对司法风险;
在不同司法区设立并联信托(但注意跨区冲突风险)。
3、时机与布局要曲线而不是一次性冲刺
提前布局、渐进转移,而非在危机前夕大规模转移;
多司法区分散风险,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兼顾流动性与保全,不应为了保全而将整个资产束缚。
4、风险评估与动态监控
定期审查信托结构与运作合规性,评估法律、税务、监管风险;
定期审查国内外司法环境变化,比如诉讼协助、破产条约、资源共享机制等;
设置信托保险、法律保障机制(如争议解决条款、仲裁条款、保险解决方案等)。

图/恒大地产,来源:网络
结语:信托终归是“工具”,不是“盾牌”
许家印案引发的最大教训或许是,信托不是万能的保险柜,更不是债务违法者的保护伞。正如坊间所流传的“信托击穿”说法,有夸大成分,但其背后的司法逻辑与制度冲击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香港法院在这一案中展现出的意愿与能力,使得长期以来“海外信托绝对安全”的幻想被打破。
真正有效的信托,必须建立在合法、透明、受托人独立、控制权合理分割、设立时机合规等基础之上。若某一环节失守,法院就可能向信托结构发起挑战。
在香港被击穿信托之后,不少人会将目光投向新加坡。新加坡信托制度在保密性、税务优惠、法律制度可预测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它也绝非不可能被越过的堡垒。无论选择哪一地作为信托架构中心,设计思路应是“提升防守成本、保持灵活性、合法合规而非钻空子”。
最后,仅凭一个司法案例无法完全否定信托的价值,但许家印案无疑成为警示篇:在全球司法趋严、跨境追索机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财富保护与传承不再是技术题,而是法治题、制度题与价值题。
当“信托”被置于光线下,越精妙的设计越容易被审视;唯有合法经营、诚信为本、精心布局、审慎运作,才能在动荡时代保住根基。
如您有这方面需求,可以联系客户经理,我们可以进一步为你梳理“若在新加坡设立家族信托,怎样设计防穿透结构”或“具体信托法条/判例对比”。马上行动起来把!
注:参考资料来源于凤凰财经,第一财经,慈善家杂志,综合新闻报道整理,转载须注明出处,侵删联系。
…
👇加V进入新加坡最大出海社群👇

往期推荐

